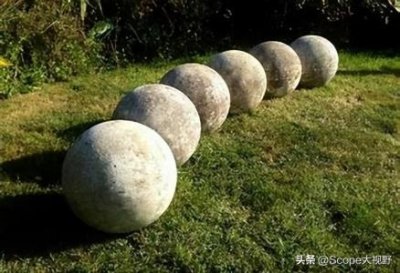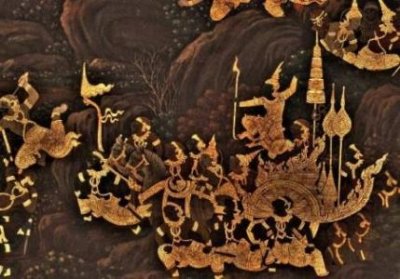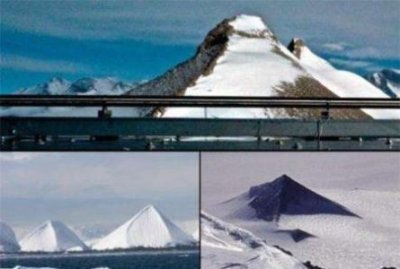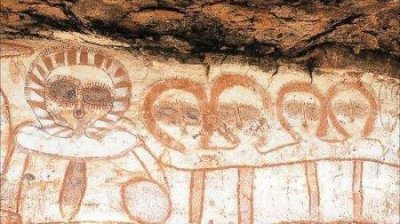滕县保卫战最后关头,白刃格斗川军手枪排吃了大亏,王师长陨落!
声明:本文内容均引用网络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,请悉知。
滕县,这座历经千年风霜的古城,在1938年的春天成了一片血与火的战场。
彼时,抗日战争的战火早已烧遍了大半个中国,而滕县,这座地处津浦铁路要道的小城,成了国共双方都难以放弃的战略咽喉。
战斗的最后一天,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站在一片狼烟中,手捂着伤口,冷冷地盯着远处围拢过来的日军。
他的眼神里没有恐惧,只有决然。
没过多久,一声枪响划破长空,这位将军倒在了城墙下,用生命诠释了“城在人在”的承诺。

为什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会牵动如此大的战局?这背后,是一场注定孤立无援的战斗。
滕县保卫战的背景并不复杂,却足够令人扼腕。1938年初,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,意图打通华北与华中的交通线,顺势包围徐州。
而徐州,是蒋介石下令“死守”的重地。
守住徐州,国军就能拖住日军,为其他战场争取宝贵的时间。
滕县作为徐州的北大门,自然成了必争之地。

川军122师奉命驻守这里,师长王铭章率领约一万人马,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。
然而,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壮的。
日军的矶谷师团装备精良,兵力数倍于守军,甚至还拥有飞机、大炮和坦克的联合攻势。
而川军,装备简陋,弹药匮乏,甚至连基本的增援都等不到。
开战的第三天,王铭章给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发了一封电报,短短几句,透着揪心的无奈:“援军未到,敌大部队已入城,即督所留部队,与敌作最后血战。”这是他的诀别信。

他知道,这场战斗的结局,只能是以命相搏。
滕县的战斗并非毫无希望。
早在战斗打响之前,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便向蒋介石请求,将汤恩伯的第20军团调来支援。
然而,这位蒋介石的嫡系却迟迟按兵不动。
汤恩伯的理由看似冠冕堂皇:他要求全军团整体行动,拒绝派一个师前往支援,理由是“避免分割零碎”。

可实际上,他心里打的算盘,是不愿意归李宗仁指挥。
这种派系之争,最终让滕县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。
川军的士兵并不清楚这些政治博弈,他们唯一知道的是,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座城。
战斗的第四天,城墙被日军炸开了口子,敌人开始涌入城内。
王铭章召集还活着的团以上军官,开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。

他的命令只有一个:进入巷战,坚持到最后一人。
然而,巷战的残酷超乎所有人的想象,子弹打光了,就用刺刀拼;刺刀断了,就用拳头砸。
到最后,川军的手枪排奉命夺回西门城楼,与日军展开白刃战。24名士兵,全部战死。
王铭章目睹这一切,愤怒和悲痛让他几乎失去理智。
他试图亲自冲上去,但被参谋长赵渭滨拦住:“师长,你不能硬拼,你要指挥!”王铭章强忍怒火,带着剩下的几名军官撤向火车站。

然而,在穿过一片开阔地时,日军居高临下的机枪像雨点般扫射过来,王铭章腹部中弹,随行的几位军官也相继倒下。
鲜血从他的身下流出,但他却挣扎着站了起来。
看着步步逼近的日军,王铭章轻蔑地笑了一声,举起手枪,对准自己的太阳穴,扣下了扳机。
他用这样的方式,守住了最后的尊严。
滕县的城墙上,县长周同还在指挥所剩无几的保安团部队与日军对峙。

这个平日里更像文人的县长,在战斗中展现出了令人意外的刚毅。
他亲自带队送弹药、运伤员,甚至在关键时刻上前堵住城门的缺口。
当他听说王铭章牺牲的消息时,沉默了许久,随后命令手下去找回师长的遗体。
他对身边的部下说:“王师长为国捐躯,这样的英雄,不能留在这片焦土中。”
然而,当撤退的命令下达时,周同却拒绝离开。

他平静地对守军说道:“人生自古谁无死?城亡与亡的县长,我愿开其先例。”随后,他独自走到城墙边,纵身跃下。
滕县,成了他的归宿。
滕县保卫战的惨烈程度,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
这场战斗,川军阵亡万余人,几乎全军覆没。
而日军为了攻下这座小城,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
然而,这一切的牺牲,并没有换来徐州战局的胜利。
历史学者曾评论,如果汤恩伯的援军能够及时赶到,滕县或许不会沦为孤城。
然而历史没有如果,派系之争的后果,最终由最前线的将士用生命买单。
有人说,滕县保卫战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,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胜败。
它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人精神,什么是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。

王铭章、周同,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,在家国危亡之际,个人的生死早已不重要。
他们的牺牲,换来了民族的希望,也让后人铭记:有些战斗,值得用生命去守护。
(免责声明)文章描述过程、图片都来源于网络,并非时政社会类新闻报道,此文章旨在倡导社会正能量,无低俗等不良引导。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,请及时联系我们,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!如有事件存疑部分,联系后即刻删除或作出更改!